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联合召开的“回归媒介本质:生成型媒介与关系重建”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新闻学、传播学、哲学、商学、文化学、艺术学、计算机学等多个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张涛甫教授等参加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孙少晶教授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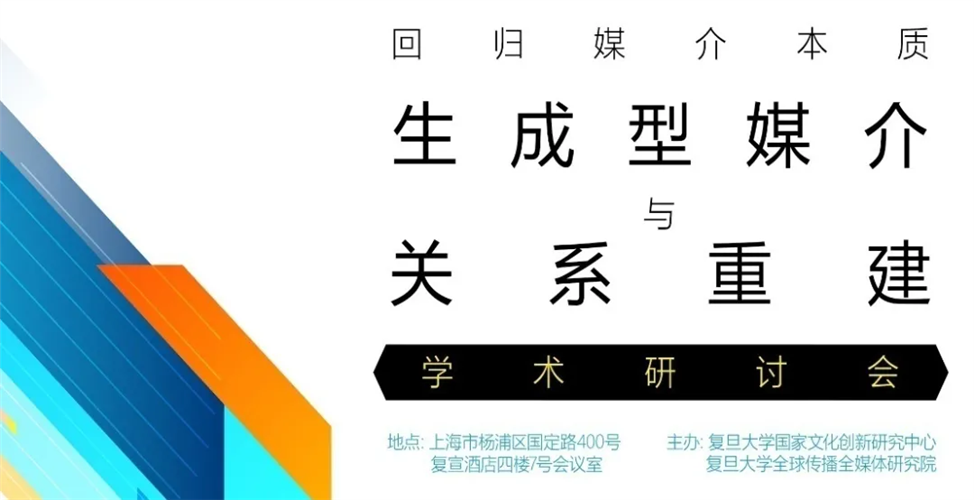
研讨会海报
当下,媒介化社会的进程正以迅不可挡之势飞速发展,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既是一场生产力的伟大变革,也是一场人类交往的伟大革命,同时,这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变革。人类向数字化时代、网络化时代的全面迁徙,是一个时代性的人类重大研究命题。处在这一研究领域,“新媒体(new media)”已经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与之相关的“新媒体研究”,更是方兴未艾。新媒体一词的极度应用和新媒体研究的持续升温,一直没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学术怀疑”和“学术警惕”,以至于“新媒体”一词的误用和“新媒体”研究的失控,给新闻传播学科乃至其它相关学科,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误导”甚至是“误用”。面对如此状况,有必要在新闻传播学术界发起一场“正本清源”的学术讨论。否则,新闻传播学科和相关的学科研究,可能会因为“新媒体”研究中的“自身遮蔽”和“有意遮蔽”,产生“以讹传讹”甚至是“谬误流传”的不良效应。“回归媒介本质:生成型媒介与关系重建”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开启一场“去蔽还原”的学术研讨。本次学术研讨会紧紧围绕针对“新媒体(new media)”而提出的“生成型媒介(emerging media)”这一核心理论概念,展开了五个层面的学术研讨,即“生成型媒介的动态维度”“生成型媒介的时间维度”“生成型媒介的融合维度”“生成型媒介的创新与再造维度”“回归本质与关系”。

研讨会现场
一、关于生成型媒介的动态维度
孙少晶教授在主持这次研讨会时首先提出:面对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有必要反映出媒介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提出了“生成型媒介(emerging media)”这个极为重要的新概念。这个概念之所以不同于“新媒体(new media)”概念,因为“生成”一方面是过程,另外一方面是结果,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媒介慢慢成型,为公众所认识和接受。研讨会首先对生成型媒介中的“生成”代表什么展开讨论。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宏秀教授指出,“生成”是一种动态性,而当下所有媒介构成当中多元性分布性恰恰是动态生成最核心的元素,从构成到生成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构成相对静态的,生成相对动态的,但是在整个媒介研究等当中,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当我们从“构成”向“生成”迈进的时候,恰恰需要从一个基础的架构视角来看其本质的意义。媒介具有调节性,不是简单的中介或者居间,我们在研究媒介时,如果把媒介仅仅当做一个居间,它的动态会缺乏很多,而中介本身在黑格尔哲学意义上是一个静态过多的东西,类似于构成和生成之间的静态和动态的差距一样,调节更能反映当下技术的主动性、能动性和智能性。来自复旦大学的张涛甫教授指出,我们必须要有对当下媒介整个逻辑分析有新的界定。这包括我们对它认知的方式。媒介也是变量,在当今变量中,知识正在流量化,媒介也在业态化。处在这时候,我们对媒介的研究关联变量变得特别复杂,这对媒介与社会的研究带来了巨大挑战。我们必须应对这一挑战,我们要以前所未有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对媒介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
关于这一问题,孙少晶教授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传统媒体时代,离身性长期占据主流,使用者或受众个体与媒介之间具有明显的间距性和区分性。但是居于离身性的传播理论对新传播技术及其传播范式的解释力日显不足,而由技术(可穿戴设备、增强现实、人机互动等)激发的身体参与性越发明显。具身性已经成为生成型媒介的一个内化逻辑,并成为一个日益走上前台的元逻辑。媒介逻辑是媒介内容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股力量,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媒介逻辑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媒介逻辑直接关系到媒介效果和社会变化。媒介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常规及仪式的一部分,媒介已经不单纯是实现某些实际功能比如信息和娱乐的工具,它们逐渐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验环境(environment of experience)。生成型媒介因为其动态性、生成性创造出与其它的体验环境相似而又不同的传播体验。生成型媒介带来的是身体的回归,主客体的合一,以及传播语境的本质彰显。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在过去更多是聚焦于单一的或者特定维度的延伸,而在生成性媒介语境中则是整体传播体验环境的延伸。因为媒介的具身性,媒介与人的互动包容性,媒介是人的延伸,人也是媒介的延伸。媒介技术发展就是人类延伸并回归的过程。通过身体主体性的媒介参与,人性回归成为可能并且是延伸的必然结果。这种回归同时预示着人类传播交流的转向,媒介传播与非媒介传播趋向合流并愈发自然化。

研讨会学者发言
二、生成型媒介的时间维度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姜宇辉教授认为,技术并不单纯是构成力量,相反是前进化的力量,是主导人往前发展变化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单纯是看到现象,或者是结果,或者是效应。媒介生成,那就是要看到主导人发展的动力,就是把技术、生命、整个社会结合在一起。生成是强调人和技术共同往前的进化,然后把技术当成推进的力量。今天人类生命的进化、社会形态的进化,跟技术还是大致同步的,它就像是两条平行线,它是共振的,可以交织在一起。所以如果技术真正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全面渗透的话,那么它就是渗透到时间这样一个维度,然后让我们认识到时间已经没有其它的可能性了,包括今天所谓实时、当下、瞬间这些东西。所以斯蒂格勒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主导的一个思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怎么去思索技术。一般我们仅仅是把技术当成是一个工具,人发明技术出来为人服务的,好像它仅仅是人的一个附属品,它当然也有很多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但总体来说它是在人之外的,对人起不到根本的破坏或者取代的作用。从斯蒂格勒角度来说,我们要改变一个观点就是不把技术当成人的从属,相反是把技术当成人的生成,甚至把技术当成是整个人类历史进化发展基本的平台或者介质。如果这样去考虑问题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单纯的说技术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当我们面对技术的时候单纯的说有希望或者绝望。我们应该更细致更深入地深入到技术的形态之内去考察它各种各样的细节,然后去玩味它这里面还能不能够去打开哪些不同的可能性与方向。斯蒂格勒在这里说的“技术还可以作为遮蔽”值得关注,技术今天已经作为遮蔽的形态了,这就是让人类往往看不清真理也看不清自身的本质,但是我们还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在最危险的地方去打开这种拯救道路的力量。就此议题,复旦大学的张殿元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他认为,新传媒技术不仅重构传播格局,也在改变传播研究生态。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学者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意味着传播学学科面向的多元性与生俱来,这决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走向必将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近年来,这种影响随着传播研究遭遇瓶颈以及其他学科对传媒研究的浸入而日趋强烈,传播学者无法拒绝这种基于媒介学、媒介化、中介化、客体间性、物质性和可供性等更为宽阔的研究旨趣诱惑而“离家出走”,结局是找寻到传播学研究的“本体论”而“重返家园”,还是迷失在其他学科展现的偌大学术空间中而“无家可归”,前途未卜。也许传播学的体系重建希望并不在于本学科,而是其他学科无意间行走在施拉姆的传播学“十字路口”的偶遇,发现传播学不仅是一道学术风景,还是一片学术绿洲,可以安营扎寨,安身立命。技术哲学、后人类学、STS、ANT等理论思想不断被传播学者引介、转译和应用,似乎让我们看到些许苗头。传播学的研究因为海德格尔、拉康、德里达、斯蒂格勒等思想家的进入而越来越抽象化,基特勒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评声响彻学术夜空,我们是否该思考当今世界和当下中国传播学是需要老子式的“虚化”研究还是孔子式的“务实”研究;是让媒介等同于人甚至超越于人,还是突破人的“界面”回归人的内在秩序;是把媒介看成是工具技术,还是看成是社会技术或身体技术。我们需要回应这些问题。

研讨会学者发言
三、生成型媒介的融合维度
上海交通大学的才凤艳教授认为,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发展会使得媒介延伸或者是说媒介本身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媒介了,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作为媒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现在智能家居的发展,包括华为、小米这些大的企业去做智能家居的原因就是在于智能家居未来的一些终端就是一个媒介的终端。比如说他们现在还有研发出来的伞。我们大家看天气预报是看手机上的APP,但是可能未来你看的天气预报就是来源于你这个伞今天闪不闪光,是闪蓝色的光还是闪红色的光还是闪什么颜色的光,这些光代表今天是下雨天气还是雾霾天气,所以他们会用一些智能家居的东西作为媒介的一个终端。一是媒介的性质要不停的延伸,到消费者身边来的这种延伸趋势。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消费者在接收信息的过程当中或者传递信息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种由原来非常主动的去搜寻信息的状态变成非常被动的状态。各种媒介会对消费者实施“包围”的状态,包括你家里的鸡蛋没了,你怎么去按一个按纽。我们有个心理学上的实验,就是说人在越短的时间内给他的材料越有限的时候,反而是可以增加他的创造力。媒介现在扩展为更大的渠道或者平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促销流都在这里汇集。当下这几个流在不同的裂变,就比如说我们原来是去超市购物的时候,你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都是发生在超市的,你进去以后才看到信息你才买,然后你付钱你拿走,所有这些都一起发生的。但是当互联网出现以后,你的信息流和你的资金流是发生在线上,你的物流的转移是发生在线下的。就这一研究议题,与会的其他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各自的学术看法。复旦大学陈阳副教授从计算机技术的角度切入了生成型媒介的研究。他认为,emerging是在emerging media里面的一个子集,就是在emerging media里面相对比较新的。而在emerging media当中的一部分是social media,social media当中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比如说比较早的Facebook、Twitter。Emerging 强调了新颖这个层面的意义,这在用户生产内容(UGC)这个语境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以自身带领团队参加的大量实践案例,来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他进一步认为,生成型媒介在网络化与数字化基础上实现的前所未有的融合,赋予了生成型媒介的显著特征。

参加研讨会学者合影
四、生成型媒介的创新与再造维度
华东师范大学的林立甲教授则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谈了他对生成型媒介的看法。他认为,生成型媒介体现出激发对象或者促进对象,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是体现着人的主体能动性特点,这与原来的媒介是极为不一样的。另外,他也认为,我们在使用生成型媒介的过程中,会赋予内容以及参与者多层面的意义。意义的增加让参与者、媒介与外界的其它事物建立关系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林立甲教授认为,心理学研究对于生成型媒介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于生成型媒介的创新与再造维度这一议题,与会的汤筠冰副教授则从视觉传播角度谈了她的见解。她认为,生成型媒介的“观看”更指向了观看主体在理性主义支配下的“用什么样的方式观看”,是区分了主客体界限的观看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视觉性”是视觉研究最为重要话题。针对视觉性研究,荷兰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米克· 巴尔认为视觉性的研究指向的不是视觉对象本身的物质性或可见性, 而是看的行为, 是隐藏在看的行为中的全部结构关系。一切观看行为得以可能的条件都应包含在这一全部结构关系之内。“视觉性”不是指物的形象或可见性,是使物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短视频、社交平台媒介为代表的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当下时空观念的异化,社交化属性进入视觉媒介,视听场景与视觉叙事被碎片为拼贴所取代。当下视觉媒介研究不仅意味着是研究对象发生了转变,也可以说是研究实践本身在媒介理论模式下被打碎甚至离散。这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生成型媒介的物质性有相似之处,物质性成为支撑媒介得以可能的一切基础设施。VR、AI等视觉技术促使视觉媒介制造出了新型的观察者,重新定义了观看者的主体性与观看对象,并消解了身体在场的必要性。“离身”式的视觉传播正成为常态。
五、回归本质与关系
闫宏秀教授认为技术是人类在世的方式,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技术化的生成,我们必须通过技术来获得当下。如果有了技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眼中的世界和技术调节过后的世界。数据智能化背景下,我们的人和技术的关系是怎样一种呈现?现在是人机融合时代,人机融合意味着什么?技术不再是外在,是向内嵌入进去,这个时候外在人造的形式我们要重新想一下,这是核心观念。生成并不是强调技术对人的强势渗透凸显技术的地位,而恰恰是在想为新技术背景下守护人之为人的本质提供理论框架,指导技术赋能,警惕人被技术取代与淹没。怎么样回归,如果一直往前走怎么回去呢?一个想法是新人文主义的想法,重新审视媒介,从构成到生成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现在强调全过程,全生命周期,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欧盟人工智能倡议书,从中获得我们可以借鉴的更多东西。闫宏秀教授还,虽然出现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数据分布式散落,相对应的分布式道德,生成性当中恰恰是分布式的一种特征和汇聚状态。和分布式道德相对应的是分布式责任,这种状态下并不是对道德以及道德责任的弱化或者消解,恰恰需要关注的是回去,回到新人文主义状态。
复旦大学的孟建教授认为,生成型媒介的“回归本质与关系”某种意义上是体现了“一种的新文化存在”。首先,生成型媒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体现着社会文化的新形态。生成型媒介建立了个人与社会的新关联,并以此为基础造就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这样认为,生成型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物的本质”为受众提供适配性极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存在。其次,生成型媒介作为一种文化变迁,体现着文化历史的新转向。生成型媒介作为文化变迁的一种动力,不应仅作为反思的对象,更应作为改变文化景观的一种重要工具。这也深度涉及了知识生产的全民化,甚至完成了“从全民知识生产权利的获得到权力的掌握”这一历史性转向的命题。这也许如同曼诺维奇所指出的,当下媒介文化界面中的大多数元素来自我们已经熟悉的文化形式,只不过是在当下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平台中发生了裂变。孟建教授特别指出,无论生成型媒介怎样体现着文化历史的转向,其不变的必须是对“人”作为精神交往主体的极大肯定。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具风采。第三,生成型媒介作为一种文化结构,体现着文化构成的新形态。在这方面,也许英国的文化理论正在逐步让位给德国文化理论。如同基特勒所言,媒介一边连接着尼采和海德格尔,另一边连接着拉康和福柯;一边连接着歌德和卡夫卡,另一边连接着爱迪生和图灵。在基特勒力图重建“人与媒介关联”的努力的背后,是生成型媒介正体现着一种“超学科”的结构,各种学科在生成型媒介上的汇流激荡,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自2015年成立伊始,就关注了媒介本质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在新媒体文化、数字人文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成立不久的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也在这一研究领域汇聚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展开了诸多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学术进展。这两个重要学术研究机构将“强强联合”,深耕这一基础领域的研究,以期通过持续的研究,获得更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